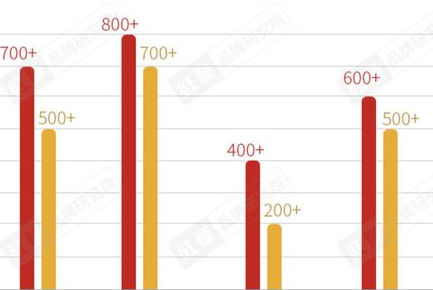傅靖生:更愿意做一只打破天平平衡的蒼蠅





《益西卓瑪》油畫
“在接踵而至的每一天里,我流連在幻夢中,安閑優(yōu)哉地度過自己的歲月,夢里不再為任何人事物駭然不已,我有萬分的清靜。其實,何須再添‘萬分’這個形容詞來描述清靜呢?光是清靜兩個字,便足以形容我的愉悅。大風大浪還是會有,但風風雨雨已經過去。”這段伊夫·納瓦爾的話,在采訪傅靖生接近結束時跳進我的腦海,和坐在旁邊的傅靖生形象重合。
而他正仰著臉、瞇著眼告訴我,不要在乎把他寫成一個什么樣的人,因為他不會在乎,“你寫的都只是我的一部分,不會是我的全部,我更愿意做一只打破天平平衡的蒼蠅。”
熱衷于打破平衡的傅靖生和難以描述的清靜重合,呈現(xiàn)給我的是“大風大浪還是會有,但風風雨雨已經過去”的姿態(tài)。他不只是導演,還是攝影師、畫家,他是一位七旬有余的藝術家。
影畫展是導演謝飛的一個創(chuàng)舉
去年12月中旬,我在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個展廳里見到傅靖生。之前我們雖然相識,但并沒有過多接觸,這一次,是導演謝飛策劃的一場展覽,促使我想進一步了解他。
展覽主題是謝飛、傅靖生電影及美術回顧展,主旨為讓觀眾從傳統(tǒng)美術歷史和技法的角度,欣賞百年來電影藝術留下的“流動的繪畫”,從這一創(chuàng)作遺產,記住在其中工作的攝影、美術工作者的藝術與成就。
何謂“流動的繪畫”?傅靖生的解釋是,電影就是。“電影才出現(xiàn)100多年,之前所有東西的形象表達都是畫,所以,電影是‘畫’動起來了。謝飛拍電影時把各種元素綜合起來,又在展覽中碎片化,便于學生吸收,悟到‘電影要有造型質量’。這個展覽展出的多數(shù)作品源自我們兩人合作的電影,是謝飛導演的一個創(chuàng)舉。”
傅靖生入學時,謝飛是剛畢業(yè)的導演系青年教員,北京電影學院是他們的共同母校。他們曾合作《湘女蕭蕭》《益西卓瑪》《黑駿馬》三部電影,謝飛任導演,傅靖生任攝影,都曾轟動一時,數(shù)個國際大獎使謝飛成為第四代導演中的佼佼者。
來觀展的人絡繹不絕,謝飛也帶著十幾位年輕人走了進來。他向傅靖生招手說:“阿傅,這是電影技術系的學生,我?guī)麄儊砩仙险n。”原來,謝飛不僅帶人來參觀,還將電影學院許多系的課堂搬進了展廳。只聽他給同學們介紹:“展覽分幾個廳。一個廳是80年代拍的《湘女蕭蕭》,其中有傅老師的攝影和木刻作品。《黑駿馬》廳,有他當時的速寫日記。《益西卓瑪》廳,有根據(jù)電影創(chuàng)作的大量畫作。后面兩個廳是阿傅的一些速寫、插圖、木刻和攝影作品。”
謝飛為這個展籌備了近三年時間,傅靖生為這個展再創(chuàng)作了幾幅大畫,比如取材自電影《益西卓瑪》的油畫《夢里黃花》,用時半年。除了畫作,謝飛還將三部電影剪輯了三個短片,有意抽去聲音,看畫面流動,分別在對應的展廳里循環(huán)放映。參觀者從中不難看出導演講故事和剪輯的精妙手法,以及攝影師對畫面和光線運用的大氣嫻熟。
傅靖生特意叮囑學生,一定要靜下心來看短片,“看什么時候切的,因為拆解是最重要的。”原來,他們當年拍電影都是當場切,而不是后來剪,“后剪沒有電影智慧,事先經過深思熟慮才好。”
謝飛心目中的傅靖生是個天才。15歲進最難考的中央美院附中學習繪畫,20歲考入電影學院學習攝影。木刻、速寫、油畫都很地道。
這兩個人互相欣賞,電影理念也趨同,都認為現(xiàn)在電影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拍起來沒有思考,原因之一是太便宜。數(shù)碼時代,沒有了膠片制約,導演容易把攝影機當成吸塵器,開關機都過于輕易。
一位解放軍抱起他問,愿不愿意和我走?
傅靖生生于1944年,出生地是浙江金華,有著頗為傳奇的身世。
他的生父黃健是一位國民黨少將軍官。1940年駐扎金華時,在防空洞里一眼看中了當時還在讀高中無線電班的章倩萍。兩個月后,黃健用兵把著,轎子抬著,把章倩萍弄到廣西家中做小。女方并不情愿,因為她正在戀愛,戀人是高中無線電班的同學,但黃健始終視她若掌上明珠。9年中,章倩萍為黃健生下5個子女,仍然拒絕跟隨丈夫去臺灣,她記恨一輩子。
傅靖生曾在文章中描述母親章倩萍的晚年容貌:臉狹而修長,顴骨低平,尖鼻頭上有高鼻梁,唇線明晰,薄薄的,紅紅的,像兩片百合,由尖長的下巴托著,是當之無愧的美人。
留在大陸的章倩萍無依無靠,日子并不好過,5個孩子的日子也不好過。傅靖生當時還叫章再鎮(zhèn),6歲開始流浪,冬天連鞋子都沒得穿。他擺過畫攤,賣過冰棍兒,金華市小,這個長相可愛的孩子沒有人不認識。
章再鎮(zhèn)10歲時,有一天在路邊擺畫攤,一位解放軍笑瞇瞇地走來,和藹地抱起他問愿不愿意跟自己走,黃再鎮(zhèn)毫不猶豫地回答:“愿意。”黃再鎮(zhèn)于是改姓傅。養(yǎng)父傅博仁大他46歲,給孩子起了新名叫靖生。意思很明顯:章旁取立,倩旁取青,左右相加為靖,這個孩子雖然改姓傅,但要記得是章倩萍所生。
傅博仁也是一名國民黨軍官,為第三戰(zhàn)區(qū)張發(fā)奎部工兵司令,第三戰(zhàn)區(qū)的重要機場工事都是他主持修建。傅博仁身份神秘,國民黨上海的防御工事是他按陳毅密令修筑。
傅靖生感嘆自己的命運中仿佛有個奇怪的八卦圖,他后來慢慢得知,傅博仁與黃健是上下級關系,而兩家原本就相識。他偶然得到過一張照片,他的生父和養(yǎng)父騎著高頭大馬在同一張照片里。
傅博仁給了這個養(yǎng)子博而又仁的愛,傅靖生回憶起養(yǎng)父母滿懷深情。他是章倩萍所育子女中生活最好的,他的兄弟姐妹有的早亡,有的做苦力,有的被單位除名……每一位都苦難成冊。傅靖生也可憐媽媽章倩萍,覺得她27歲離開丈夫,獨自拉扯那么多孩子,只求一家老小都能活著,該有多少委曲求全。
成年后,傅靖生曾將生母接到北京家中同住。“她一到我哥哥去世那天,就關起門來不說話,只聽見她在屋里嗚嗚地哭。”養(yǎng)父母聽著哭聲也難過。
傅靖生提起媽媽章倩萍去世前的一件事,令我對他由衷生起敬意。他在醫(yī)院陪媽媽時,看到病房門口總有一位白發(fā)老人流連徘徊,“我妹妹告訴我他是一個退休工人,對媽特別好。我馬上明白,他可能是媽媽的最后一個男友。”于是他趕緊過去,跟老人握手,感謝他。
“我那時候特別希望我媽媽有好多朋友,都曾經對她特別好過。”傅靖生又抿緊了嘴,安靜地看著我,四周的空氣似乎停滯了。他忽然又說:“我當時想在人的命運之上,任何人和事都是難以譴責的。而人,為什么會有惡念呢?”
通過畫筆,感到自己了不起
時代總有自己的運行方式,它總要將一些人、一些事納入自己的軌道。傅靖生在遇到養(yǎng)父之前,已和嶺南畫派名家陳松平學畫幾年。最初他只求畫畫掙錢,因為需要生活。陳松平是徐悲鴻的弟子,他免費讓孩子們在他的畫室上課,講的都是西畫,傅靖生當時就感到那是藝術的高峰。
跟隨傅博仁之后,傅靖生開始享受正規(guī)教育。先上山東省實驗中學,功課非常好,常考第一名,但他腦子里始終只有一個念頭,上中央美院附中。那是陳松平告訴他的:去北京,讀美院。
15歲時,傅靖生自己坐火車從濟南到北京,考美院附中,之前“根本沒想過考不上,好像就是去上學”。
美院附中的高質量造就了一批天之驕子,傅靖生成績優(yōu)異,畢業(yè)時卻面臨抉擇,因為那一年中央美院不招生。上不了美院去哪兒呢?正巧,時任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的吳印咸到附中選學生,在看到傅靖生的畢業(yè)作品——連環(huán)畫《捉鬼的故事》后,很是激賞,告訴他你可以做電影,愿不愿意上電影學院?傅靖生二話不說就去了。
所有的老師都認為他可惜,認為少了一個畫家,傅靖生卻覺得,那是老天給他的一條最輝煌的路。“因為繪畫和電影是沒法比的,電影是傳媒金字塔的塔尖。我也沒有放棄畫畫,電影的多元性使我大開腦洞。”
貢布里希說:實際上沒有藝術,只有藝術家,他們是男男女女,具有絕佳的天資。更為難得的是,他們是具有正直人格的人,絕不肯在半途止步,時刻準備放棄所有省事的效果,放棄所有表面上的成功,去經歷誠實的工作中的辛勞和痛苦。
傅靖生實踐著藝術家的人生之路。
1970年,傅靖生曾在張家口學生連勞動,一個偶然機會讀到一本《印象派畫史》,深受啟發(fā)。他開始效仿莫奈、雷諾阿、畢沙羅,追逐陽光去寫生。
顏料從來不缺,因為他為村里畫巨幅毛主席像,剩余顏色可以自我利用,他在跑光的相紙上刷白漆制成油畫紙。一天的時間他分成晨曦、日出、上午、中午、下午、傍晚、暮色七個時段,每個階段又分為順光、側光、逆光三個角度,30分鐘出一張畫。
他說寫生不同于攝影,要一筆一筆畫,生怕記不準變化,因為變化凝聚在每秒中。時間久了,他對光線變化產生了強記憶,對光熟知到下意識的程度,認知也從古典畫家深淺變化的素描美中走了出來,感受到太陽變化的色溫下風景所擁有的不同色調。
在張家口的寫生,好像就是為了等待《黑駿馬》
傅靖生畢業(yè)分配到農業(yè)電影制片廠。1980年他被外借拍了一部在行內影響很大的彩色寬銀幕故事片——《追索》,攝影絕佳。這部片子后來成為電影學院七八班的觀摩教材片。
謝飛通過《追索》找到了傅靖生,那是1986年。
兩人關系一直不錯,“文革”時在電影學院都屬聯(lián)委會派,謝飛是干部子弟,傅靖生缺生活費時還常受他的接濟。謝飛請傅靖生為《黑駿馬》擔任攝影師。而在傅靖生心目中,謝飛的智慧和品質都是超人的,而且對畫非常熟悉,知道畫畫的人攝影肯定也是好的。
拍攝《黑駿馬》時,傅靖生在天蒼蒼野茫茫的內蒙古大地上,徹底玩了把外光電影。“我們追逐太陽,追逐光線變化,那里像是塊離天最近的地方。我在張家口的寫生,好像就是為了等待這部片子。”
在《黑駿馬》展廳,有傅靖生的一段文字說明,他說自己是從文藝復興繪畫大師的作品中找視覺依據(jù),大師們的畫是光的遺產和審美的坐標。達·芬奇的蒙娜麗莎畫面只有一個漫射光源,看不見明晰的投影,畫面純凈,變化微妙,縱深影調豐富且神秘。還有維米爾、倫勃朗的油畫。他以這些畫為坐標,確立了內景《黑駿馬》的用光原則。外景則依據(jù)印象派,致力于保護外光的冷色。
拍攝條件艱苦,但氛圍愉快。劇組工作按部就班,有條不紊。謝飛安排演員走完戲,設計好鏡頭,傅靖生便去選景,選角度,預測第二天出發(fā)的時間,一切準備妥當,“做好拍攝打算,是我的職責,從來不是著急搶時間,都是非常準確地到那兒,所以我們一點都不累,剩下的時間大家就打撲克。”
拍攝期間他寫拍攝日記,優(yōu)哉游哉。“在拍攝完最美的光線后,剩余時間就用線條和語注追憶有意思的生活點滴。”
其中幾則:8月24日,大雨將至,從(屋子)縫里鉆進的大小蒼蠅每天有一個兵團,免不了大打出手。
8月25日,草原的狗愛吃糖,因為草原的水硬,而糖里有酸,狗吃糖能中和堿。(拍攝時)狗不愿隨小孩下山坡,我給它吃糖,再扔一塊下山。于是,它追糖下山,我們拍攝。要是劇組再待上半年,這狗非得糖尿病不可。
9月18日,前晚有霞,滿天星斗,子夜后起西風積云而無星,晨五時只剩三縷積于東地平線,呈紫灰色,天幕由白變微黃,七時出發(fā),周邊山林仍浸于藍色(色溫13000K)。七時半,西山頭露橘紅色,霞光(色溫2500K),遂以東邊50米高山作逆光暗背景,作臨界照明。
“吸引眼球、嘩眾取寵的東西我們一概不做。”
在沒有監(jiān)視器即顯效果的年代,唯有攝影師第一時間知道銀幕效果,所以除了嚴格的技術把控之外,在案頭階段,最重要的是攝影師把想象中的電影和導演想象的盡可能靠近,再用圖片表述出來,進行討論和切磋。在現(xiàn)場,導演只看表演,只有攝影師知道畫面。拍攝完畢膠卷打包,送回北京沖洗,印成樣片,到專門的放映間放映,導演才能看到。傅靖生說:“所以導演和攝影師之間的信任非常重要,而且我確實值得信任。我會告訴謝飛各種方案,他不采用我也不生氣。”
展廳墻上的一張照片中,傅靖生正在拍一個雪景。雪嘩嘩地下,他穿條褲衩站在水里拍,“這很辛苦吧?”我問。“當時都沒有,特別幸福。”他答。
謝飛在傅靖生心目中最大的特點是拒絕仇恨,他認為這很不得了。“我在他的電影里學到了原諒感。”的確,看他們合作的三部影片,大愛是其中的主元素。1994年的《黑駿馬》,謝飛淡化了性的原動力,更強化生命感。1999年的《益西卓瑪》,三個男人跨越了女主角益西卓瑪?shù)囊簧瑥碗s的故事被處理得水乳交融,理在情中,“這樣的鴻篇巨制,非謝飛莫屬。影片中透露出的善良,令人蕩氣回腸,那來自于謝飛拒絕仇恨的基因品質。”傅靖生感嘆。而《湘女蕭蕭》在愚昧鄉(xiāng)俗之外對新生兒的樸實接受,更體現(xiàn)出人性的包容。
《益西卓瑪》根據(jù)藏族作家扎西達娃的小說《冥》改編,藏族人基因中的大愛和善良無仇像檀香沁入傅靖生的心扉,使得他拍出的每一幀畫面都像油畫。傅靖生說,他和謝飛都徹底反對暴力美學,“吸引眼球、嘩眾取寵的東西我們一概不做。”
傅靖生用肩扛移動的方法拍過許多電視劇,自拍自導。
和濮存昕、許晴合作《來來往往》和《說好不分手》,傅式導演的方法基本采用激活式。他和濮存昕都認同“話劇是嚴謹、準確、不許動的;電影是一次性表演。”尊重這樣的創(chuàng)造原生態(tài)理念,雖然是電視劇,也拍得如入無人之境。
傅靖生認為濮存昕是天生的表演藝術家,雖然沒有讀過專業(yè)表演院校,但受父親蘇民影響很大。“他和他父親,就像師父帶徒弟。”
傅靖生去看《李白》,清晰地記得一個畫面:濮存昕瀟灑熟練地念著“將進酒”,曲終時“啪”一摔水袖,隨即對著坐在前排的傅靖生點了一點手,“我當時就驚住了,驚嘆于他的揮灑自如。在那樣毫無污染的月光下,他創(chuàng)造出了最好的自然美。那場戲我非常喜歡。”
忙完手頭事情,想專心寫小說
傅靖生的藝術創(chuàng)作涉及諸多領域。
他喜歡玩插圖,認為文學作品沒有插圖就像人臉沒有五官。活動的影像拍麻木了,更喜歡讓人物凝固在紙上,看不夠。
他選擇版畫作為與影視平行的創(chuàng)作,認為一張好圖片去掉中間層次,強化反差后必是一張好版畫。他給我解釋,珂勒惠支的自畫像是最好的說明,明暗永遠相隨映襯,實在是極好的影調訓練方法。
上世紀80年代后期版畫愈漸孤寂,許多版畫家開始做各種嘗試,尋找轉機,傅靖生把注意力轉向了剪子和紙。
“我學剪紙,不按中國傳統(tǒng)的格式剪,而是受馬蒂斯啟發(fā)。他的每一張抽象剪紙都始于生活中某一具象的點,張張有個性。我限制了抽象度,在形和意之間拿捏分寸,以求畫中的動物在人列之中,多少有些活脫的幽默。馬蒂斯只剪不印,我剪完后涂墨色印宣紙,獨創(chuàng)的方法叫‘軟紙水印’。”
進入晚年,他的小說、劇本已經有160萬字,他也不著急,想在手頭事情忙完后,用剩下的時間回老家去寫《白鹿原》那樣的小說。“我爺爺是廣西當?shù)赜忻拇蟮刂鳎易骞适绿貏e有意思。”
他也愛虛構人物,創(chuàng)造是他的頂級享受。他并不想把文字變成復雜的電影,寧愿在一方白紙上自個兒畫畫、寫東西。
他囑咐我記住一點:只有你是自己的依靠,比如愛上了寫作,筆就是你的依靠。世界上99%的人把喜怒哀樂帶進了墳墓,1%的有心人寫下來,就是文學藝術。其實帶進墳墓的某些素材,比我們的經典著作要經典。
他有時邋里邋遢,有一次在家門口的過街天橋上東晃西晃,被人當成拾荒老頭抓住,其實他是在看構圖。
兒子傅鶇也是導演,父子倆心意相通,有事他會傾全力幫忙。去年傅鶇拍的網(wǎng)絡劇《九陰白骨爪》貓眼上熱度第一,他很是安慰。
七旬有余的傅靖生回望半生路,覺得基本畫了句號。電影學院之后的漫長生涯,他沒有向我詳述,我只知道他無論在學校還是工作后,因為生父和養(yǎng)父的身份都受過委屈。他告訴我,突然在某一天懂得了與歧視相伴,“因為我必須活著,冬天已經來了,就不怨冬天,自個兒取暖就是了。如果不懂得這個,可能會充滿怨氣和仇恨,什么都做不了,而我是要做事的。”(記者/王勉 供圖/傅靖生)
- 傅靖生:更愿意做一只打破天平平衡的蒼蠅
- “關燈吃面”開年15家公司爆雷 490億身價女富豪被立案調查
- 解禁洪潮襲來 中遠海控解禁市值200多億
- 明星基金踩雷長春高新 抄底游資、北向資金均被埋
- 盒馬8888元的整頭年豬火了 有的還贈送“黃底花鳥鍋”
- 押注國潮文化俘獲年輕人的心 新中式點心豐富消費場景
- 穆迪:預計2022年,特斯拉的自由現(xiàn)金流將大幅增加,2021年的預估為31億美元
- 穆迪:隨著2022年制造能力的增加,特斯拉將繼受益于全球電動車的需求增長
- 加拿大外交部網(wǎng)絡遭攻擊 持續(xù)五天仍未完全恢復
- 越南VN指數(shù)開盤幾無變動至1439.71點
- 商務部:2022年促進消費持續(xù)恢復
- 印尼主要股指下跌1%至6588.61點
- 歐洲地中海地震中心:北大西洋發(fā)生5.5級地震
- 澳大利亞2021年第四季通脹激升,市場猜測澳洲聯(lián)儲提前加息
- 商務部:新能源汽車銷量達到352.1萬輛,比上年增長1.6倍,每賣出8輛新車就有一輛是...
- E-迷你標普500指數(shù)期貨3月合約跌1.04%,納斯達克100指數(shù)期貨跌1.41%
- 里約克拉羅-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東部142公里處發(fā)生5.3級地震
- 日本東證指數(shù)上午收盤下跌2%至1890.77點
- 山東黃金股價上漲
- 商務部:穩(wěn)住外貿外資基本盤在六個方面發(fā)力
- 商務部:2022年將修訂擴大《鼓勵外商投資產業(yè)目錄》
- 現(xiàn)貨白銀日內跌幅達到1.00%,報23.75美元/盎司
- 韓最新數(shù)據(jù):2021年近60多萬韓國人放棄求職,創(chuàng)下2014年以來新高
- 商務部:確定2022年為“外貿鞏固提升年”
- 商務部:中國外貿產業(yè)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
- 商務部:部分國家刺激政策過快退出可能會引發(fā)需求萎縮
- 日本經團連會長淡化統(tǒng)一加薪,稱企業(yè)應依本身情況決定工資
- 今日美股 | 道指盤中狂瀉1115點后反抽,新能源汽車股重挫
- 杭州公布首批48家“未來工廠” 看看都有誰?
- 蔚來涉足新能源車險業(yè)務,斥資5000萬成立保險經紀公司
- 傅靖生:更愿意做一只打破天平平衡的蒼蠅
- “關燈吃面”開年15家公司爆雷 490億身價
- 解禁洪潮襲來 中遠海控解禁市值200多億
- 明星基金踩雷長春高新 抄底游資、北向資金
- 盒馬8888元的整頭年豬火了 有的還贈送“黃
- 押注國潮文化俘獲年輕人的心 新中式點心豐
- 穆迪:預計2022年,特斯拉的自由現(xiàn)金流將大
- 穆迪:隨著2022年制造能力的增加,特斯拉將
- 加拿大外交部網(wǎng)絡遭攻擊 持續(xù)五天仍未完全
- 越南VN指數(shù)開盤幾無變動至1439.71點
- 商務部:2022年促進消費持續(xù)恢復
- 印尼主要股指下跌1%至6588.61點
- 歐洲地中海地震中心:北大西洋發(fā)生5.5級地震
- 澳大利亞2021年第四季通脹激升,市場猜測澳
- 商務部:新能源汽車銷量達到352.1萬輛,比
- E-迷你標普500指數(shù)期貨3月合約跌1.04%,納
- 里約克拉羅-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東部142公里處
- 日本東證指數(shù)上午收盤下跌2%至1890.77點
- 山東黃金股價上漲
- 商務部:穩(wěn)住外貿外資基本盤在六個方面發(fā)力
- 商務部:2022年將修訂擴大《鼓勵外商投資產
- 現(xiàn)貨白銀日內跌幅達到1.00%,報23.75美元/盎司
- 韓最新數(shù)據(jù):2021年近60多萬韓國人放棄求職
- 商務部:確定2022年為“外貿鞏固提升年”
- 商務部:中國外貿產業(yè)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
- 商務部:部分國家刺激政策過快退出可能會引
- 日本經團連會長淡化統(tǒng)一加薪,稱企業(yè)應依本
- 今日美股 | 道指盤中狂瀉1115點后反抽,
- 杭州公布首批48家“未來工廠” 看看都有誰?
- 蔚來涉足新能源車險業(yè)務,斥資5000萬成立保